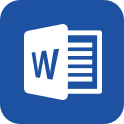金箍棒是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第一道具:孙悟空造反时,它是反抗天庭的兵器;孙悟空取经时,它是维持秩序的工具。
在野时的孙悟空,以花果山为根据地,举兵造反,自称“齐天大圣”,公然以武力对抗天庭。而取经时的孙悟空,已被招降,不仅皈依了如来、观音的佛教世界,而且服从了玉皇大帝的天庭势力。此时的孙悟空,既以认同、归附、保护现有格局为前提,则他手中的金箍棒,无论对付的是妖怪还是歹徒,几乎都体现为治理工具,其功能更像是某种法律。
起初,金箍棒只是水利建设的工具。东海龙王向孙悟空介绍说,金箍棒原“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西游记》,下同)因此也叫“天河镇底神珍铁”。孙悟空也曾对玉华州小王子这样说,“鸿蒙初判陶F铁,大禹神人亲所设。湖海江河浅共深,曾将此棒知之切。”由此可见,金箍棒从最初测量水文的仪器,后来变为衡量人与妖、正与邪、善与恶的法律工具,也就可以理解了。
赴西天取经,是佛界与唐朝共同实施的一个宗教交流项目,需要可靠的安全保障。将孙悟空从五行山下“解放”出来,正是为了建立以金箍棒为标志的法律保障体系。金箍棒的威力毋庸置疑,作为曾经的拥有者,东海龙王不无恐惧地说,“那块铁,挽着些儿就死,磕着些儿就亡,挨挨皮儿破,擦擦筋儿伤!”取经路上,唐僧、八戒被狮驼岭的妖精吓破了胆,孙悟空却充满了“金箍棒自信”,“我把这棍子两头一扯叫‘长’,就有四十丈长短;晃一晃叫‘粗’,就有八丈围圆粗细。往山南一滚,滚杀五千;山北一滚,滚杀五千;从东往西一滚,只怕四五万压做肉泥烂酱!”
金箍棒作为保障取经的法律工具,能否发挥作用,外部环境非常重要。西天路上,金箍棒知名度并不高,玉华州的小王子肉眼凡胎,不知金箍棒的底细,豹头山的黄狮精也同样不识铁棒的庐山真面目,它将悟空、八戒、沙僧的“行头”一并盗去,举行的竟然是“钉钯大会”。如果说在玉华州没有遇到识宝人,那么,在金兜山遇到的却是老对手,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就曾吃过金刚琢的亏。金箍棒胜不了金刚琢,孙悟空打不过青牛怪,金箍棒遇到了克星,其实质是道教系统对佛教系统的干扰,“金刚琢体制”对“金箍棒体制”的掣肘。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竟然是如来与老君私下沟通、暗通款曲的结果,不无讽刺意义。
如将金箍棒视为法律工具,就要以其作为划定人妖、正邪、善恶的价值绳墨。一般说来,死于金箍棒下的都应属于妖、邪、恶类。然而,并非所有的妖、邪、恶类都会死于棒下。不必怀疑孙悟空的忠诚与正义,也不必怀疑金箍棒的神通与威力。比如隐雾山的豹子、七绝山的蟒蛇,在这些妖怪面前,金箍棒代表了法律,体现了正义,因而所向披靡,战而胜之。而在白骨精问题上,由于权力干预法律,感情凌驾政策,就是金箍棒,也不免忍辱负重,含冤受屈。
面对神通广大、作恶多端的妖魔,如狮驼国的大鹏雕、朱紫国的金毛辍⑵蕉ド降慕鹨童子,金箍棒不仅没有任何优势,反而为其所制。此时的金箍棒,不是不代表法律,不是不体现正义,这些妖魔之所以逃脱惩罚,完全由于保护伞所致。保护伞下的妖魔,其危害往往大于草莽妖怪;妖魔的保护伞,其地位与神通往往在孙悟空之上。法治既然不济,孙悟空只得越级上访,到西天求告人治。如何看待这些保护伞?在黑风山上,孙悟空对变成妖精的观音开玩笑,“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菩萨笑道:“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奥妙其实在此。
如果说金箍棒代表的是法律,孙悟空的身份是执法者,那么,六耳猕猴这个手持假金箍棒的假孙悟空,则冒充着正统,亵渎了法律,亵渎了正义,但竟而骗过了天宫、地府和观音,打乱了如来、观音建立的法律体系。这是如来不能容忍的。这也是六耳猕猴一定死于金箍棒下的基本道理。
金箍棒的全名是“如意金箍棒”。不过,这“如意”二字是有选择的。取经路上,金箍棒曾经两度易手,一在玉华州,一在金兜山,却并未“如”新主之“意”。它只是“如”悟空一猴之“意”而已。金箍棒在孙悟空手里,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这为孙悟空留下了太多的自由裁量权。鉴于金箍棒随意变化的特性,一会儿成为绣花针,一会儿成为金刚钻,缺乏了法律本身应有的定性与刚性,难免不让人产生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