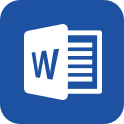基于想象界的镜像阶段的主体只看到自我虚幻的统一性,将他人误认为自我从而成为一种异化主体;而进入象征界的主体则能够认识到主体与世界的分裂性,承认自我根本上是一个他人。小说主人公奥吉・马奇是犹太人后裔,周围的各种人物都企图把他的命运纳入自己的公式:在事业和生活理想上,他不断地受人摆布,成为一个“他人”。劳希奶奶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来左右他,她一面教给马奇说谎的本领,一面又说要把他培养成能讨有钱人欢心的绅士;富商伦林夫妇则想让他当义子,把他“造就得完美无瑕,十全十美”;而他的亲生哥哥西蒙一心想把马奇培养成他的副手,并且像他一样“不必去管别人死活,只要你自己能得到好处就行”。同时,在爱情上,马奇也不断遭遇到“爱人”的摆布,一次次地迷失在情人的甜言蜜语中。豪门千金露西希望马奇能够成为经商奇才,入赘豪门;而泼辣任性的西亚则要求马奇和她一样喜欢驯化鹰捕捉蛇。马奇为了获得自己“更好的命运”曾一次次地落入别人的圈套,他们都试图打着事业、生活理想、爱情的幌子来影响改造马奇,诚如马奇所说:“从我出生的那天起,所有这一切都在等着我。他们试图对我施加影响,规划我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布满圈套的社会里,马奇不可避免地迷失了“自我”,成为了“异化着的个体”(拉康93)。
欲望真正的对象是缺乏之物。同时,因为欲望浮现的初始便是依附于他人,所以欲望含有一种根本的他性,欲望是他人的欲望。马奇终其半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命运,“然而,寻找自己的命运和寻找自己的父亲似乎又是一对难以分离的连体婴。”(廖七一5)美国著名比较神话学家坎贝尔论述道:寻找父亲与寻找自己的命运密切相连。个人的身体和心智是母亲给予的;而性格却要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性格就是你的命运,所以寻找父亲就是象征着寻找自己的命运……”在马奇还未出生的时候,马奇的父亲就已经弃家出走了,威严,专横的父亲角色却由种种类型的训导者出现。霸道、严厉的劳希奶奶是马奇家的主宰,也是马奇的第一位“家长”,马奇虽然内心反抗她抵触她,但是却不得不事无巨细地处处听命于她,大到工作,劳希奶奶为马奇“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贝娄,《奥》35),小到生活细节处处严格要求马奇。艾洪则是马奇“所认识的第一个伟人”,艾洪就是马奇精神上的父亲。在马奇以后历经人生的大事时,总是询问艾洪的意见,如同一个儿子对父亲一般。而艾洪也是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一般,参加马奇的毕业典礼,在马奇误入歧途的时候引导马奇走正道。如果说劳希奶奶是马奇童年时候的保护神――“父亲”,艾洪就是马奇青少年时期的“父亲”。他们提供的生活方式虽然安全稳定,但是个体却没有自我选择的自由。因此马奇并没有得到他一直渴望的父爱,他的欲望追求是“无所获”的。他曾经感叹道,那些人会想着为他好而没完没了地责怪他,这样子,他又多了一个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而他却要摆脱的人。
在充满诱惑的世界中, 马奇并没有随大流选择 “捷径”,他“历险”的半生,也同样可以说是他反抗“同化”,维护“自我”的半生。他知道“个性是不安全的,安全的是类型”,但是他仍然寻找自己命运的归宿。其间不免历尽千辛万苦,但是文章最末他却如同哥伦布般的骄傲。
参考文献:
[2]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3]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4]廖七一:《论奥吉・玛琪历险记的神话母题》,《外国文学》1994年第1期,第5-9页。
[5]索尔・贝娄:《奥吉・马奇历险记》,宋兆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