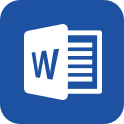摘要:要想理解和翻译好being,并在理解和把握being的问题上超过自古以来的西方哲学界的研究水平,我们必须连续进行下列六个逻辑转换:一,being是英语单词的代表;二,词是语言的代表;三,语言是人类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主要物质化方式之一;四,所谓的思维过程就是人对客体进行主观处理的过程;五,所谓的主观处理就是人对客体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和描述的过程;六,西方哲学界两千多年来不断追问什么是being,其所起的真正功能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主观处理,以及主观处理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西方哲学;being;主观处理论;ontology;本体论
凡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都知道,being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理解和翻译的英语单词。由于正确理解和翻译好这个单词涉及汉语是否能真正消化好两千多年来多种西方哲学理论的问题,所以今天还是应该多花一点时间继续讨论一下如何正确理解和翻译好这个单词的问题。
王路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上发表论文时指出,“我们中国人有足够的能力用汉语来表达和把握有关being的问题,关键在于突破尚有欠缺的知识结构,超越固有的狭隘眼界。”[1](P39)此论非常正确。
笔者认为,要想理解和翻译好有关being的问题,并在理解和把握being的问题上超过自古以来的西方哲学界的研究水平,就必须连续进行六个逻辑转换,或者说把握好六个相互关联的命题或认识。它们分别是:
一、being是英语单词的代表;
二、词是语言的代表;
三、语言可以表达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语言是人类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主要物质化方式之一;
四、所谓的思维过程就是人对客体进行主观处理的过程,思维的结果就是人对客体进行主观处理的结果;
五、所谓的主观处理就是人对客体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和描述的过程;
六、西方哲学界两千多年来不断追问什么是being,其所起的真正功能是在不断地追问什么是主观处理,以及主观处理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西方哲学界本身至今还没有对being做出一个合适的公理化认识,还没有对being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属加种差式”定义,其主要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与他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把握好这六重逻辑转换,或者说与他们还没有完全概括好这六个相互关联的命题或认识有关。
一、主观处理就是人对客体进行多
方面多层次的考察和描述 迄今为止,中外哲学界一直还未给主观处理这个概念给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属加种差式”定义。人们目前对主观处理这个概念的理解还停留在将主观处理视为人的精神活动,或者说人的意识活动的水平上。换句话说,人们还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我们人类能够说,只有人类具有主观处理能力,只有人类具有精神活动,只有人类具有意识活动,而其他动物都不具有这类能力。这表明,中外哲学界对主观处理这个概念的认识还处在较低层次的阶段。
笔者认为,所谓的主观处理,就是指主体在自己的思维过程中对客体进行多种多样处理的过程。首先,主体可以对同一事物进行抽象程度不同的概括和描述。例如,我们可以把我家饲养的一只猫称作是“一只家猫”,也可以称作是“一只公猫”,“一只猫科动物”,“一只食肉动物”,“一只哺乳动物”,“一个脊椎动物”,“一个脊索动物”, “一个生物”,“一个东西”,等等。在没有给定思维前提的情况下,即在没有给定思维对立面或者说思维限定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对这只猫的种种称呼都是正确的,都反映着这只猫的某种属性,都反映着这只猫与世界上其他存在物之间的某种联系。
我们之所以可以对同一事物进行抽象程度不同,或者是多角度的概括和描述,是因为我们常常需要根据我们在不同场合的不同需要来对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属性进行片面的考察、思维和表达。例如,当我把我家饲养的一只猫称作是“董志勇家的一只猫”时,我是从社会所有权的角度来考察和表达我家饲养的那只猫的。当我把我家饲养的一只猫称作是“一个生物”时,我是从我家饲养的那只猫是否具有与自然界之间进行自主新陈代谢这种功能的角度来对它进行考察、概括和表达的。
主体对客体进行多种多样处理的另一种典型方式是我们可以对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属性进行虚构和假设。例如,在几何学中,我们可以虚构没有面积的点,没有宽度的线,没有体积的面,并进行相应的计算。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所虚构的,在上天居住着玉皇大帝等众多神仙一事,也是我们中国人对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属性进行虚构和假设的一个典型事例。自古至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进行这种虚构和假设的事情比比皆是,天天都有,俯首可拾。
此外,不同的主体可以因其自身利益的关系,对同一个客体做出性质完全相反的主观处理。例如,对同一商品的价格,顾客和商家就可以做出性质完全相反的主观处理。顾客很可能认为该商品定价太高,而商家则很可能认为该商品定价太低。甚至还有同一个商家有可能今天认为该商品定价太低,不利于自己赚取更多的利润,明天又有可能认为该商品定价太高,不利于自己通过扩大销售量这一手段赚取更多的利润等情况出现。上述种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主体确实有不同于主观的地方。这是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在同时同地对同一客体都会有同样的认识。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类为了把握事物的一些属性,常常在自己的思维过程中使用主观否定的方法。例如,我们在把握一个物体的运动速度时,需要在我们的头脑中把相关的参照物假定为处于静止状态。如当我们需要测定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的速度时,我们必须暂时无视该汽车行驶的路基正在随着地球的转动,而正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一客观事实,必须假定该汽车行驶的路基是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再如,当我们把一只家猫说成是一个生物时,我们实际上需要暂时无视存在于家猫身上的其他属性和可以描述的内容,如家猫具有脊椎,是脊椎动物,等等。在几何学中,我们虚构没有面积的点,没有宽度的线,没有体积的面,也是我们使用主观否定方法的一种存在形式。 所谓的主观处理过程还是一个主体暂时不将自己的相关肢体活动付诸行动,从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将自己的精神活动与自己的肢体活动暂时相互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已被我们人类自己称作思维、思考、推理、认识或计划等含义相类似的概念。例如,我现在就在头脑里考虑几天后或者是几个月后如何把这篇论文投稿的事宜。再如,近数十年来不同国家之间所签订的许许多多关于如何分配和利用南极洲、地球外层空间、大洋深层矿产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公约,就是人类在事先考虑今后千秋万代如何在南极洲、地球外层空间、大洋深层进行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例证。
人类对客体进行主观处理的原因,或者说人类在自己的思维过程中对客体进行方式多种多样处理的原因是,只有事先在我们的头脑中对客体进行方式多种多样的处理,事先对客体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和分析,我们人类才能准确地把握,或者说比较准确地把握客体,从而为我们人类更好地利用客体提供主观方面的条件。例如,工人在制造我所使用的木质书桌之前,起码要先从制造原料的材质,即是否是木头、尺度大小、硬度、干燥度等方面对制造书桌的原料进行考察和了解,否则就可能无法制造出合格可用的木质书桌来。
在今天人类还不能与其他动物进行直接的思想交流的情况下,人类在自己的思维过程中对客体进行方式多种多样处理的过程是可以被人类自己客观地感觉到的。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制造出自然界永远进化不出来,而且目前其他动物也制造不出来的产品来,如电脑、导弹,等等。人类在自己的思维过程中对客体进行方式多种多样处理的过程还可以通过人类所使用的复杂的语言表达系统和千千万万种文字语言表达方式来表现,而且还能被有关的听话人和阅读人的感觉器官所感觉到,进而被他们所理解和把握。其他动物虽然也有一些通过发出声音传递消息和情绪的能力和现象,但它们通过发出声音传递消息和情绪的能力要比人类通过发出声音传递信息和情绪的能力差得多,简单得多。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人类所使用的,比其他动物的简单发声复杂得多的口头语言表达方式,尤其是文字语言表达方式来表现和证实。质的不同来自于量上的不同,质变来自于量变。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于质和量之间关系的正确描述,确实是我们认识人类思维与其他动物的本能直觉之间质的不同的锐利思想武器。[2](P469~471)
二、语言是人类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
的主要物质化方式之一 人类进行主观思维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自身的客观实践。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人类为了更好地、更有效率地进行自身的客观实践,都是通过分工这一环节来进行群体实践的。为了更好地进行分工和群体实践,人类必须进行思想交流。但是,直到今天,人类个体所进行的思维活动还只能被进行思维活动者本人所直接知道,而无法被其他人类个体以及其他动物的感觉器官所直接感觉到。为了进行思想交流,人类必须借助于语言这一工具。这是因为语言是人类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主要物质化方式之一,它是人类经过千千万万年的进化而取得的具有社会性的自然能力之一。一个人的思维过程或者是思维结果,只有通过使用肢体语言、口头语言或者是文字图像语言,才能被其他人类个体的感觉器官所直接感觉到,然后再通过其他人类个体的思维过程而被其他人类个体所知道和理解,进而再组织起有效的分工和合作。例如,笔者对主观思维这一概念的思考和认识,就可以通过笔者的文字语言和口头语言表达出来,从而被其他人类个体的感觉器官所直接感觉到,然后再通过其他人类个体的思维过程而被其他人类个体所理解和把握,从而使简体汉语文化圈的人都能确定主观处理这一概念的内容和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以汉语为载体的哲学理论体系,以便我们能够进一步进行相应的更高一级的群体实践。
人类之所以需要将人类的主观处理过程语言化,尤其是将主观处理过程文字语言化和图像化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每一个历史上具体存在的人类个体和群体,其记忆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例如,我个人就常常记不清楚我在这篇文章前面部分由我自己所写的具体的文字表述。在我不能通过几分钟的思维就能完成这篇文章所要表述的全部思想观点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完整和逻辑内恰地表述这篇文章所要表述的全部思想观点,我就需要将我已考虑过或者是已经考虑好的那部分思想观点先用文字记载下来,以便我在后来的思考和写作中能够准确地知道我在这篇文章前面部分已经考虑和表达过的那部分思想观点。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叶蜚声等人在其著述的《语言学纲要》中,曾对类似情况有过这样的论述,“实际说话的时候,句子是不会太长的。因为太长了,说话的人(或听话的人)说(或听)到后来会忘记前面说过(或听过)的内容。”[3](P20)这段论述清楚地说明了每个人的记忆力都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把我们的思维过程文字语言化,我们才能进行比较深入的逻辑推理和思维。
对于一个人类共同体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每一个人类共同体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构成的。由于每一个具体的人类共同体所包含的人类个体数量总是有限的,再因为每个人类个体的记忆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每一个历史上具体存在的人类共同体能够凭借其全体成员大脑直接记忆的东西也都是有限的。
此外,对于每一个人类共同体来说,该人类共同体已经获得的对该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有利的思维结果,如各种思想观点、知识、思维方式方法、语言表达规则等等,还需要传给后代成员,以使这一共同体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所以,每个人类共同体都需要将对该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有利的思维结果进行物质化处理,即通过使用相关的文字、图像或者是口头语言等客观物质载体,将这些思想观点传给后代成员。
外国学者在研究逻辑学时,也常常是通过分析人们的一些语言表达现象来分析人们所进行的一些具体推理到底是好的思维和论证,还是坏的思维和论证的。[6](P5~8)
三、being是英语单词的代表
当代中国词汇学家认为,词是语言中最小的意义单位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7](P26)虽然词同语音语法一样,都是运用语言不可缺少的内容和条件,但是“词汇系统又比语音、语法系统复杂得多,直到现在,人们也感觉对词汇的系统难以把握”。[8](P189)加上许多语言的词汇量大得惊人,例如英语仅通用词就有十万左右,汉语《辞海》一书所收录的词条也有十余万条。如果再算上专有名词,如毛泽东、长江、黄河,等等,简直不可胜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词是语言的代表。
每个懂得一些英语的人都知道,其实在每本稍微大一点的当代英语词典中,作为being词根的 be的种种用法,都已被解释和说明得清清楚楚。即使有人有不知道或者是不懂的地方,也完全可以通过查字典搞得清清楚楚。那么为什么一些哲学家还要继续着力研究作为be的总括的动名词形式being呢?其次是,当代英语通用单词已有十万个左右,为什么西方哲学界单单垂青be,并单单把它的总括,动名词being作为研究的重点呢?能够证明当代西方哲学界单单把词根be的总括being作为研究重点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当代西方哲学界的两个重量级人物海德格尔和萨特,就是因为曾着力研究being,并分别出版了《BEING AND TIME》[8]和《BEING AND NOTHING》[9]这两部著作才被当代世界哲学界所格外推崇的。
此外,be是英语系动词中用途最广,最为“能指”的一个系动词。人们在许多场合可以用它来说明英语的其他主要系动词,如the word of ‘seem’ is a common linking verb(seem这个词是一个常用系动词)。而其他系动词则往往难以做到这一点。
再者,作为助动词的be,可以用其各种具体变化形式,如be、been、being、am、are、is、was、were等与相关动词的过去分词合用,共同组成英语的被动语态,如The book is being read by someone(这本书正有人在看),等等。而这一功能是所有其他英语主要助动词,如shall、will、have、do等所不具有的。而作为助动词的be,却和shall、will、have、do一样,可以用其各种具体变化形式,与相关动词的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共同构成表示动作发生时间的各种时态。
此外,在当代英语中,原为动名词的being,在一些场合已被转用为与系动词功能几无联系的名词,用以指代前面已说过的事物和东西,或者是人人都知道的事物和东西,如those beings(那些东西),human being(人类),等等。
词根be也是目前英语动词中保留变化形式最多的一个词根。其他英语动词在与前面的单数主语名词搭配使用时,一般都已将动词变化形式合并为三,仅仅使用动词原形加s或者是es,以及动词原形加ed这三个变化形式,如the color of the apple changes fast,the color of the apple changed fast,用以表达与主语相配套的单复数、人称和时态。而be在与前面的单数人称主语名词搭配使用时,却保留am、are、is、was、were等五个变化形式,如I am, you are, he is, she was, you were,等等,用以表达与主语相配套的单复数、人称和时态,等等。 用中国汉语词汇学的术语来说,以上情况表明,英语动词词根be的动名词形式being,是英语中义素最多的一个单词。[7](P29)由于英语动词词根be是目前所有英语动词词根中功能最强,使用频率最高,保留变化形式最多的词根,所以笔者认为,英语动词词根be的动名词形式being完全可以被当作英语单词/词语的代表来对待。
四、如何正确翻译being和ontology
根据笔者目前对英语语法以及西方哲学的了解和理解,being一词出现翻译困难的地方,主要是在翻译英文What is being这句问话中,以及在一些专门研究作为词根be的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确切含义的论著中。在其他涉及使用being的英文文献中,翻译水平稍微高一点的翻译者都能根据所译文献的上下文,找到适当的汉语词语来对being进行正确恰当的翻译。该翻译成“是”的时候,他们自然会翻译成“是”; 该翻译成“存在”的时候,他们自然会翻译成“存在”; 该翻译成“有”的时候,他们自然会翻译成“有”;在仅仅起表达时态的作用,该省略不译,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时,他们自然也会省略不译。相关的中国读者在阅读时也没有发现有逻辑不通,或语言不通的现象,或者是有读不懂的地方。几百年来中外学者所翻译过来的千千万万本英国文学作品和各学科的专业论著在中国的命运已经非常鲜明地证实了这一点。
以往的有关论著大多认为,在What is being这句问话中的being,以及在专门研究作为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确切含义的论著中的being之所以难以翻译,主要be的含义和在英语中所起功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作为它的动名词,其含义来源也是多种多样的,其所含义素太多。他们还认为,虽然由于being可以被当作英语系动词be和英语助动词be的动名词形式来使用,因而可以被做主语来使用,从而为英美人士研究be的种种用法和功能提供了方便。但是,由于be的含义和在英语中所起功能多种多样,所含义素太多,致使中国人乃至不少以拉丁语系其他语种为母语的人,也都不知道到底选择be的哪一种含义和be在英语中的哪一种功能为好了。再如,我国当代学者汪子嵩和王太庆曾在一篇论文中介绍说,我国第一个将古希腊文中相当于being的词语翻译成“是”的学者陈康先生就曾认为,古希腊文中相当于being的词语“在中文里严格讲起来不能翻译”。[11](P15)陈康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being所含的义素太多。
笔者认为,上述解决being翻译问题的思路有缺陷。这个缺陷就是,这是一种把问题仅仅推向具体一端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虽然可以为最后重新概括和抽象某个问题或概念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方法也导致了问题的头绪越来越多,最后出现难以进行更高一级的概括和抽象的结果。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两千多年来对词根be的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研究就处于这种状态。我们使用把该问题推向具体一端进行分析的方法,其目的还是为了最后能够进行更高一级的概括和抽象,以提高日后的演绎推理和实践水平。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一种好的分析方法了。所以笔者认为,目前要想解决好being的正确翻译问题,更需要使用把该问题推向更为抽象的一层,也就是推向更为抽象的一端的方法。这推向更为抽象的一端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连续追问,既然being是一个词,那么什么是词呢?既然词是语言的一个构成成分,那么什么是语言呢?既然语言是人类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或者说是人类进行主观处理和表达主观处理的主要物质化方式之一,那么什么是思维呢?当我们连续解决了这几个问题时,我想我们也就非常容易解决什么是作为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这个问题了。
笔者认为,西方哲学家几千年来一直要不断提出什么是词根be的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实际上是想知道什么是主观处理,也就是什么是思维,以及主观处理或者说思维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笔者提出这一观点的根据是,虽然说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所含义素很多,但即使being所含义素再多,当今每一本稍微大一点的英语词典或者是英语百科全书,以及相关的英语语法书籍,都已将这些义素罗列得完完全全,清清楚楚,根本用不着再去探索什么是作为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确切含义的问题。即使是古希腊语,也曾将相当于英语词根be的单词on的各种使用方式、变化形式和义素罗列得完完全全,清清楚楚。[12](P48~54)所以说,西方哲学家几千年来一直不断提出什么是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这一问题,肯定是另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他们不断提出什么是being的问题的直接原因就是,英语词根be的多种变化形式和多种使用方法,能够充分表现出人类对语言的多种多样的处理方式,从而表现出人类主观处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他们还没有概括出什么是主观处理,以及主观处理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命题的情况下,他们只好以追问作为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确切含义这一方式来代替追问什么是主观处理,以及主观处理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了,因为这样的做法是人类思维比较容易达到的,这是因为对现象发问,总是比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容易一些,总比透过现象找其中规律性的东西要容易一些,总是比找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要容易一些。
笔者认为,应当尽快把ontology汉译成“主观处理论”。这是因为,每一本稍微大一点的英语词典都明确写明,ontology是研究being的一门学问。而西方哲学界几千年来研究being的真正目的,或者说最终目的,其实就是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主观处理,以及主观处理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到底什么是主观处理,以及主观处理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就完全有理由把ontology的汉译改为“主观处理论”。虽然我们不能把What is being翻译成“什么是主观处理”,但是我们却完全可以把ontology汉译成“主观处理论”。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把握了西方哲学界几千年来研究being的真正目的和内容。仅仅翻译单词与翻译一个句子中的同一个单词到底还是有所区别的。翻译一个句子中的单词时,该单词要受所在句子前后文的影响。仅仅翻译单词则可根据人们使用该单词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处理就行。各国各种语言词典中所列举的同一个单词的多个义项这件事,已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此外,把ontology汉译为“主观处理论”,还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更好地理解being和西方哲学传统,有利于我们中国人更好地理解包括辩证法在内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我们中国人在此基础上更快更好地完成主观辩证法的公理化过程,从而使我们汉语圈对辩证法的研究能早日全面处于世界的最前列。
但是,要想做好把ontology汉译改为“主观处理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想做好这一改变,最起码还必须相应地阐述好“本体论”的正确汉译英问题。但是要阐述好这一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事情。由于论文篇幅的关系,只能以后另文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