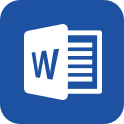摘 要:清末民初,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写情小说出现,哀情小说是其中一个支流。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发表于刚创刊不久的《礼拜六》,以悲凉无望的爱情悲剧为结局,由此奠定了周瘦鹃后来一贯的写情风格。通过细读该作,可以发现周瘦鹃小说中的“哀情”产生于社会转型期新旧道德观念的矛盾与冲突。
关键词:周瘦鹃 《此恨绵绵无绝期》 哀情 矛盾
周瘦鹃早期的作品经常发表在《小说月报》和《礼拜六》这些杂志上。《礼拜六》可以称得上“鸳鸯蝴蝶派”的阵地,“翻开任何一期《礼拜六》都会看到一片‘情’字,成为了该刊的一种特色”①,而“真正能代表《礼拜六》言情小说水平的是周瘦鹃的哀情小说”②。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写作哀情小说成为一种创作潮流,周瘦鹃也卷入了这个潮流中,由于经历了与周吟萍(英文名译作紫罗兰)的感情变故,使他创作的哀情小说有着浓厚的感情基础,他自己也说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有一半与紫罗兰有关。“所谓哀情小说,其特点在于‘哀’和‘情’两个字,它表现了爱情中的悲哀无望以及悲凉的结局,既含宿草之悲,再下哭花之泪,风格哀感顽艳,凄婉动人。”③
以往的哀情小说多是写婚姻的不幸造成的家庭悲剧,这种不幸主要来自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周瘦鹃的此篇《此恨绵绵无绝期》一改往日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写作方法,以自叙的方式来叙述妻子纫芳与丈夫宗雄的新式爱情故事。虽然也以悲剧收尾,但是造成悲剧的原因已经冲破了家庭门第观念,而源自一次偶然的社会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的故事虽是悲剧,但已经认识到传统婚姻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弊端,在当时可谓一种进步。周瘦鹃的思想与“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家相比显然更加保守,但是与前人相较,他的小说已经开始注意爱情的本质和内涵。
小说的男主人公宗雄是受西式教育的青年,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在国家危难之际不顾儿女情长,挺身而出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在战斗中投入满腔热情以致背部受伤导致瘫痪,最终没能陪伴妻子纫芳走完余下的人生。可是在受伤的情况下,宗雄仍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余下的人生,顽强地与病魔做着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夫妻二人“寓野外一精舍中,上下仅二三间”④,生活简单并不富裕,却仍然“郎鼓批亚那,妾唱定情歌”⑤,夫妻间感情融洽,这是以爱情作为基础的婚姻,两人互相尊重,相濡以沫。作者写这样的情境,可见女性的地位在当时社会是受到重视的。宗雄与妻子“或操琴,或唱歌,或猜灯谜,或弄叶子”⑥,都表现出了二人对生活的热爱,且婚后生活的美满幸福。宗雄是有着丰厚的知识、思想开明的人,在新婚时,他为妻子作《My darling! I love you》一歌,并且通体英文,也在妻子读到“安琪儿”一词时,告诉妻子那是天使的意思,这些都说明了宗雄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两人参加朋友的聚会时,宗雄的目光几乎一刻不离妻子的身影,对身边的其他女性不肯多看一眼,这是对妻子最真挚的爱的表现。
由于宗雄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他在思想上自然也受到了西方观念的影响。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能长久,却不以中国传统的礼教约束妻子,同时,他生前还开明地为妻子计划将来,把妻子托付给老同学洪秋塘,无处不体现着他对妻子深沉的爱。周瘦鹃对这一情节的书写,足见他冲破了封建伦理制度的牢笼。中国在封建制度下经过了几千年的岁月,儒家的伦理纲常已经深入人心,“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更是早已被人们接受认同,周瘦鹃在这样的情境下,描写了宗雄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开明的人物,不愧是一种进步。
作者对宗雄、纫芳命运的描写,抛弃了以往才子佳人惯有的结局,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结尾,而钟情于哀情、惨情、悲情,更加突出了“情”的重要地位,也更能够吸引读者。
洪秋塘是宗雄和纫芳结婚后被宗雄第一个介绍给纫芳的朋友,足可证明他在宗雄心中的地位有多重,“他无所好,第好读书”{16},在宗雄备受病痛煎熬的时候为宗雄带来了很多新说部和杂志,以帮助宗雄排解病痛的苦恼。他同样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文化洗礼的青年,这可以从他在家中举行舞会,为纫芳弹琴等细节得到证明。也就在频繁出入宗雄家探访朋友的期间,他对纫芳心生爱慕,小说中写道纫芳给洪秋塘递茶杯时水溅到手上而低呼,他听到后关心的急切询问是否是因为自己接得太快,说话时眼中还出现了不该有的异样神情。又如他送红玫瑰给纫芳时,把纫芳比作白玫瑰,并不再称呼纫芳为“嫂”,这些细节都流露出他对纫芳的感情,已从以往的朋友之情转变为对心爱女子的爱慕。他不在乎儒家礼教规范的束缚,敢于面对来自封建观念的挑战,按照自己的思想意愿做事情。当然,这也归功于他有一个思想开明的母亲。洪秋塘的母亲已经年过五十,但是仍旧穿着华丽的服装,甚至呈现出一种“娇态”,他的母亲和年轻人一样参加舞会,对纫芳的事情了解后,也没有像封建家长一样对儿子的终身大事加以干涉阻挠。在清末民初阶段,社会虽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但是封建观念犹存,在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中,虽有民族美德的精华,可是封建思想的糟粕也掺杂其中。伴随着西方思想观念在我国的逐渐渗入,人们的思想也开始走向开放,尤其是受到西式教育的青年一代,然而,虽被西方观念不断影响,但是仍旧不能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娶寡妇为妻仍然是忌讳。虽然“封建的等级伦理观念,也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自由平等的空气更为浓厚……贞节牌坊开始被砸毁,人们的思想来了一次大解放”{17},但很少有人能够认同《娶寡妇为妻的大人物》中所写的“娶寡妇为妻,既无损于本人的名誉,也无碍于本人的事业”{18}的观点。可是洪秋塘并不避讳这些,仍旧愿意接受宗雄的托付,面对纫芳,在洪秋塘的眼中可以读出和宗雄一样的热情。洪秋塘从外归来到宗雄家中,没有看到故意避开的纫芳,便会垂问去处,在他的心中,纫芳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纫芳的关心不亚于宗雄。纫芳为丈夫请医生时,他仍会说:“纫芳,吾之安琪儿!吾来此与君别也,脱再居此者,寸心且为汝碎矣!”{19}从洪秋塘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纫芳的爱已经不亚于宗雄,他不忍看到心爱的女子伤心难过,看到悲伤的纫芳他便会心痛不已。虽然他愿意接受宗雄的托付,娶纫芳回家,在纫芳余下的人生中,承担照顾纫芳的责任,但是无法面对纫芳的悲伤。面对一个即将成为寡妇的人,他的爱如此炽烈,可见洪秋塘的爱是多么的真挚,他的思想是多么开明。
产生于辛亥前后的哀情小说,因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与以往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的喜剧结局略显不同。以周瘦鹃为代表的哀情小说作家,大多经历了动荡的社会变革,这些熟读儒家经典的思想教育家和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来自异域的新鲜元素,他们通过翻译西方小说,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文化,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创作理论,了解了西方的悲剧创作,走上了哀情小说的写作之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才子佳人们‘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20}
通过阅读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我们不难理解作者的心理矛盾在小说中的体现。宗雄与洪秋塘这两个受西式教育的青年,代表了接受时代改良的作者。周瘦鹃把他们二人描写成思想开明,敢于追求爱情、冲破封建牢笼的青年,面对来自传统礼教的束缚,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斗争反抗,或不要求妻子为自己“守节”,或愿意接受自己喜欢的寡妇,这代表了一种思想的进步,显然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纫芳形象的塑造,十分能够表现中西文化冲突下作者的矛盾心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中西文化既冲突又融合,既排斥又接受的大背景下嬗变,中西伦理道德的差异使之经常产生强烈冲突”{21},在塑造纫芳形象时,一方面,他希望人们在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思想得以解放,摒弃封建伦理制度的糟粕;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女性依旧是男性的附属品,希望女性依旧遵从儒家礼教典范。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本想赞颂身为妻子,自始至终对丈夫不曾改变的深深的爱恋,颂扬夫妻间生死不离不弃真挚爱情的一面,可是这样的结局又不免给读者留下生搬硬套的感觉。作者在赞颂美好爱情的同时又落入了俗套,把封建礼教呈现给读者,降低了小说的质量,这是近代社会特有的矛盾导致的,也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带来的结果,小说作家们从林纾翻译的《茶花女》中得到了悲剧写作的启示,看到了外国小说中爱情的自由平等,本想模仿,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影响,最终没有逾越中西文化差异下,对爱情领悟差距的鸿沟。虽然周瘦鹃的这篇小说是在这样的矛盾冲击下完成的,但却奠定了他写情小说的创作基石,小说中宗雄对妻子的深情、纫芳对丈夫的爱恋,打动了读者,赢得了眼泪,也构成了周瘦鹃这篇哀情小说的全部。
①②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4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3}{16}{19} 周瘦鹃:《此恨绵绵无绝期》,《礼拜六》,中华图书馆1914年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