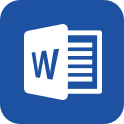在利率市场化基本落地的前提下,银行业关于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的议论甚嚣尘上。监管层是否需要在新的宏观背景下去积极适应银行业基本面的变化而有所作为,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表外融资、借道理财等渠道不再奏效的情况下,增加信贷投放的必要条件就是取消存贷比监管。在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前,存贷比作为流动性监管指标有其必然性;随着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完成,存贷比监管已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渐进式调整非一蹴而就
其实,从存贷比监管指标的历史变迁来看,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渐进式的调整和改变。
国外的银行并不将存贷比纳入流动性监管指标,美国银行业当前存贷比在75%-77%之间,以美国银行业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水平来看,银行业并未将贷款扩张到较为激进的水平,信贷扩张自有其边界。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银行信贷收益率高于同业、债券等其他资产,银行通过提升信贷在生息资产中的比重可以做到提升整体资产收益率。
在存贷比监管指标取消后,商业银行存贷比最高只能达到约80%。商业银行需要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目前,这一比例约在20%左右,从而存贷比最高也就80%左右。
若存贷比监管指标取消,在极端情况下(按照80%存贷比测算),16家上市银行将新增人民币贷款约6.6万亿元,也就是可释放出6.6万亿元的信贷。存贷比较低的银行,如南京、兴业、农行等,能够释放出的新增贷款较多。
基于2014年年报制作的存贷比上升后对生息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分析,选取的数据均为银行日均存款、信贷及其他生息资产数据,假定银行一次性将信贷规模提升至最高存贷比水平,同比例替代除存放央行以外的其他生息资产,新增贷款收益率水平与前期平均持平。
不同的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提升幅度不同,主要基于两个指标:一是贷款与其他生息资产收益率差;二是当前存贷比水平。农行、平安、宁波、南京的收益率提升水平相对较高,而工行的收益率提升也较可观。
以上分析是在不考虑信贷的收益率变化、不良率、拨贷比以及其他成本(如风控管理成本)的情况下对生息资产收益率的简单计算,银行在存贷比放开后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决定贷款扩张策略。
存贷比监管指标取消后,银行信贷投放规模提高,资产配置结构将调整,高息的信贷资产替代其他低息的资产,净息差回升,从而影响到银行利润表,提高盈利能力,提高ROE。
我们可以采用以下的简化测算方法来测算存贷比取消对银行利润的影响,银行资产的收益率=信贷资产占比×信贷资产收益率+非信贷资产占比×非信贷资产收益率,存贷比取消后,银行信贷资产占比提高,而非信贷资产占比下降。
存贷比取消后,银行增加信贷规模,必然消耗资本,我们按照以下的方法测算了在极限情况下,信贷规模扩张对资本充足率的消耗。
如果各家银行都将存贷比达到临界值,从行业平均来看,资本充足率大约下降1%左右。其中南京、农行、平安、宁波、工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程度最为明显,这里的测算方法相对复杂,但如果按照简单的方法测算,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流动性宽松促信贷扩张
存贷比限制取消放松了银行信贷规模的限制,银行可以通过将投资、同业等生息资产替换为收益率更高的信贷资产从而提升整体收益率水平。但在当前的宏观经济与银行经营条件下,银行的信贷扩张仍有诸多限制因素。
首先,经济下行条件下社会信贷需求不足,信贷的边际风险收益比提升较快;其次,信贷与非信贷生息资产的收益率提升在综合考量不良率、拨贷比之后,利润增厚效应不明显,再次,银行业实际存贷比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准,加上“影子银行”,主要融资需求实质已经得到满足,信贷增长空间主要在零售、新兴产业、中小产业等领域,银行进入需要一个过程;最后,银行业的信贷扩张仍受制于资本充足水平。 总体而言,银行业在存贷比限制取消后信贷规模不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将进入一个缓慢提升的过程。而在宏观经济环境好转的情况下,以上制约银行信贷扩张的情形将出现好转,新增信贷的边际风险收益水平下降,银行可以实现通过信贷扩张提升业绩弹性与ROE水平。
此外,未来替代存贷比作为流动性监管指标的LCR与NSFR相较存贷比更加重视对流动性实质的监管,有助于降低银行业的实质性风险。
《巴塞尔协议III》中对LCR与NSFR的描述为:流动性覆盖率(LCR,Liqudity Covered Ratio)= 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流动性覆盖率的标准是不低于100%,这个公式的意义在于,确保单个银行在监管当局设定的流动性严重压力情景下,能够将变现无障碍且优质的资产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这些资产可以通过变现来满足其30天期限的流动性需求。
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Net Steady Finance Ratio) = 可用的稳定资金/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净稳定资金比率的标准是大于100%,这个公式的意义在于,用于度量银行较长期限内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对其表内外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该比率的分子是银行可用的各项稳定资金来源,分母是银行发展各类资产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来源。分子分母中各类负债和资产项目的系数由监管当局确定,为该比率设定最低监管标准,有助于推动银行使用稳定的资金来源支持其资产业务的发展,降低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
除了以上分析贷款增长对生息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之外,放松存贷比还具有以下两个效应。
第一,银行经营管理从负债端转为资产端。作为一项监管指标,存贷比一直是银行不敢逾越的雷区,由此也催生了存款冲时点、违规揽储、金融掮客等乱象。尤其在互联网金融、股市火爆的背景下,存款逃离银行的趋势已难以逆转,银行的对存款的追逐成本上升较快,放松存贷比,替代为实质性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使银行可以更加纯粹的根据自身业务开展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避免特定监管指标对业务的干扰。
第二,表内扩张和表外扩张同步。过去通过银信、银证合作将信贷转为表外的现象随着存贷比的放开以及监管的日趋严厉而有所下降,总体上看目前银行理财中融资类占比已经在持续下滑,未来占比可能更低,银行理财将更大程度上摆脱融资功能,成为实质的资产管理者。但从短期来看,信贷资产出表的节约资本消耗、无需计提准备等优势仍然存在(融资类理财实质就是一个简版的资产证券化),即便放开存贷比限制,其需求仍然存在。
目前,就上市银行而言,从综合信贷/非信贷资产收益率差与当前存贷比水平看,平安、农行、宁波、南京通过提升信贷规模改善收益率水平的可能性最大,有望短期受益于监管的放松。
存贷比背后的宏观意义
作为一项银行业务监管的微观指标,存贷比监管看似对宏观层面的意义不大,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存贷比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增加人民币贷款,提高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占比。随着人民币贷款的增加,也将提高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进而提高M2同比增速。由于外汇流出导致外汇占款减少,基础货币投放规模在下降,需要通过降准、增加信贷投放规模的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提高M2增速。
存贷比的取消将减少信贷投放中间环节,降低贷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率。表外融资方式,无论是信托贷款,或者是委托贷款,其融资成本率都高于贷款。随着表内信贷投放规模的增加,且信贷投放中间环节减少,企业获得低成本融资方式,有助于降低社会平均融资成本率领。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管理层竭尽全力促使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逐步显现。在连续降准、降息后,只有银行向实体经济发放贷款,信用创造的机制才会发挥作用,M2增速才会提高。
最后,从国家战略先行的角度看,银行机构和信贷资金必然会随着国家战略方向的改变而不断跟进。这里主要包括,其一,华夏银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成立专项资金,主要支持环保、基建、科技、产业转移等;其二,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中行计划提升中银国际在东盟区域的功能,计划把东盟地区部分分行银行业务和资产并入中银香港中,使其成为“一带一路”东盟地区相关业务的主办机构。另外,中行还公布了海外业务发展战略,计划通过自设和并购在新兴市场国家多设网点,使其海外资产和利润占比目标要达到 40%,而今占比只有25%。其三,适应国家产业输出和能力输出的对外发展战略,交行将并购巴西的BBM银行,顺利入主巴西金融市场,加快国际化。
随着地方政府融资方式迎来新时代,低成本资金也将流入实体经济。近期,江苏和新疆成功发行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获得低息资金,部分将用于置换平台贷款,不再用于基建投资等,这些资金都将逐步低成本流入实体经济。
存贷比监管指标取消后,银行业基本面将又迎来一重大利好,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即使以前也存在多种渠道规避存贷比监管,但规避和完全取消意义完全不同。
与对利润的影响相比,存贷比取消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更为明显,资金开始低成本流向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投资规模也会增加,经济企稳对银行资产负债端的改善更为明显。
5月18日,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务成功发行,事实证明,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的置换一定会非常顺利,压制估值抬升的最后一根稻草消除。在第一批地方债务置换启动后,第二批置换的事宜也紧锣密鼓地提上日程。
根据媒体报道,第二批债务置换额度与第一批额度一样,仍为1万亿元,额度已经下发到各个省份。此前,有消息称,财政部考虑第二批地方置换债券初步额度设定在5000亿-1万亿元人民币。不过最终额度还可能调整,且需要国务院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