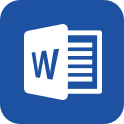一场豪赌
姚思廉也害怕,不过越是害怕,他越不能走。他也不是不知道李渊的实力,但隋朝待他不薄,他得效效忠、表表心:若被唐军杀死,他就是殉国;若能侥幸活下来,他就赚了。生死关头,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
汹涌的唐兵果然在姚思廉面前停止了前进。他们当然不怕他,怕的是他的说法:“唐公起兵的本义是要匡复皇室,你们不得对代王无礼。”
这番言辞太讨巧,姚思廉给李渊戴上了高帽子,将他由“犯上”说成“靖难”。唐兵愣住了,这些人虽粗鲁,却懂得一个道理:主子虽然觊觎帝位,却藏着掖着,从来没挑明,自己犯不着冒泡当替死鬼。加之他们对这个老头儿惺惺相惜,便都肃立在堂下,不敢胡来。
李渊赶来了,看到了这场力量悬殊的对峙。姚思廉替他脸上贴金,他哪能给脸不要脸?连属下都顾忌这种君臣大义,明智如他当然不会做傻事,况且代王还是他的王牌――贸然称帝毕竟有篡位之嫌,得有个傀儡禅让的缓冲,才能让李唐战车软着陆。
于是,在李渊和唐兵意味深长的注视下,姚思廉扶着代王走下了大堂,孤独而镇静地走向他们的临时住所顺阳阁。安顿好代王,姚思廉哭得一塌糊涂: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这些,之后,无论形势如何发展,他都无能为力了。
代王对姚思廉自然感激不尽:姚思廉保护了他的生命,维护了他的尊严。李渊父子对姚思廉也赏识有加:姚思廉忠义刚烈,大唐正需要这样的直男。坊间更视姚思廉为坚贞不二的忠勇哥,到处宣传膜拜。至此,姚思廉完成了一石三鸟的艰巨任务。
这场豪赌还让姚思廉看到了李渊父子的胸襟和耐心。姚思廉毕竟是隋臣,唐代隋后,他是做旧朝遗民,还是做新朝臣子?这个选择让他很纠结,虽然他以前也经历过两次改朝换代,但陈代梁时他刚出生,隋灭陈时他24岁,只做过藩王的幕僚,并未接近权力中心。唯有隋朝这个被李渊拥立的隋恭帝(即代王)让他柔情百结,难以割合。
是李渊让姚思廉下了决心。在沉默的对峙中,李渊的眼里满是欣赏和敬意。从姚思廉大义凛然地给自己戴高帽子起,从姚思廉从容地扶着代王走出大堂起,李渊就认定,这个忠直的臣子,自己要定了。
面对李渊强悍而温情的进攻,姚思廉屈服了。对隋朝,他已尽力了,何况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父亲未完成的《梁书》《陈书》正等着他续写呢……或许,顺势而为才是硬道理。
十八学士
姚思廉出生于文史世家。祖父好文史,更是个名医,救人无数,也赚得盆满钵满;父亲爱书成癖,13岁就崭露头角,年长后成为陈朝吏部尚书,更是著名学者。隋灭陈后,隋文帝夸姚父是自己平陈的唯一收获。因为姚父在梁、陈、隋三朝都任过史官,隋文帝便让他修前代史。可惜,梁、陈二史尚未完成,博学的姚父就去世了。好在有儿子姚思廉继承衣钵,姚父大可瞑目。
耳濡目染,姚思廉少年时就是史学达人,在陈朝时曾任衡阳王府法曹参军、会稽王主簿等职,入隋后,他任河间郡司法书佐。父亲去世后,隋炀帝成全了他,不仅让他继父志修史,还让他编撰250卷的历史地理著作《区宇图志》。然而,隋朝太短命,短命到姚思廉还没有完成修史任务就土崩瓦解了。
好在李渊父子惦记着他。李渊称帝后,把姚思廉留给了儿子李世民。其时,李世民搞掂了割据军阀王世充,李渊一高兴,就允许李世民设府置官。于是,李世民开馆延士,招揽延聘了18位有韬略、通文史的博学之士,是为秦王府十八学士。
十八学士当然不是纯粹的学术沙龙,除了史学家姚思廉,还有谋士杜如晦、房玄龄……他们的待遇很高,出有车、食有鱼,后来他们的画像还被悬挂在凌烟阁上,出足了风头。
刚开始,李世民也做做样子,讨论讨论学术,研究研究经籍,后来就干脆直奔主题,跟核心人士房玄龄、杜如晦等研究怎样逆转二皇子身份,成就一番大事。当然,这些事,他不会让所有学士都知道,毕竟在任何时候,圈子都有中心和外围之分。
而姚思廉能跻身十八学士之烈,很大程度上也是沾了直男形象的光。他的胆略、机智、辩才、忠勇让李世民极为赏识,这样的官员楷模,大唐需要,李世民更需要,尤其是在和亲兄弟博弈的微妙时刻,一个旗帜人物就能抵挡千军。但姚思廉的作用也仅限于此:一个性格太光明的人,怎能让他知晓太多的内幕?
李世民率军赴鲁南征讨一支隋末农民起义武装时,还不失时机地对部下进行政治教育,他举的例子就是合身护主的姚思廉。末了,他不顾姚思廉远在洛阳,巴巴地派人赏赐姚思廉300段丝帛,并抒情道:“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这和凌烟阁画像中对姚思廉的赞词“临危殉义,余风励俗”交相辉映,将姚思廉打造成了一个良史加节臣的经典形象。
秦王恩遇如斯,叫姚思廉如何不感动。他回报的方式只有一个:像忠于隋朝一样忠于李唐,忠于秦王。
五年后,玄武门兵变成功,李世民战胜兄弟和自我,登上了皇帝宝座。随行的十八学士也修得正果,姚思廉从太子洗马升迁为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专心修史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修前代五史,以魏征为秘书监,以姚思廉为主编,修撰陈、梁二史。
唐高祖曾下诏修撰过前代六史,其时,姚思廉只是修《陈史》的三人之一,《梁史》更是与他无缘。只是,唐初百废俱兴,史料阙如,加之统筹不当,分工不明,这次修史到最后竟不了了之。到太宗时期,这项工作才又被提上议程。
此时,当初的那些难题都已不是问题:太宗的人脉是现成的,十八学士都是顶级史学高手;史料经过多年征集,也基本齐全;分工到人,明确合理。这些有利条件宣告了唐初史学鼎盛时期的到来。
在贞观初年,姚思廉其实也没闲着。他修撰《唐高宗纪传》,粗成30卷,成为长孙无忌等人编纂武德、贞观二朝史的蓝本,更成为他之后修前代史的本钱。修梁、陈二史是父亲的遗愿,也是太宗委派的工程。比之高祖乱点鸳鸯谱的史学断层,这种奉诏修史的史学接力更让姚思廉感到太宗的恩遇。他只有尽心写下去,酬父志,报君恩。 不过,修史是艰苦的,虽然姚思廉站在父亲的肩膀上,但他还是感到吃力。史料的选取、观念的更替、唐朝的政治需要……这些,都需要他去仔细思考,谨慎抉择,精心架构。所幸,经过七年的努力,《梁书》《陈书》终于杀青。太宗很高兴,赏赐他彩绢500段。
重修前代五史是唐初的治国方针:资鉴。姚思廉的史书当然要符合这个前提。他“垂鉴戒,定褒贬”,总结古人经验,评价是非得失,力图以写史来影响世风。此外,他还要为李唐代隋讨个说法。姚思廉的说法是“人事观”,他借梁、陈、隋的政权更替陈述了“国家兴亡取决于人事治乱,而非天命”的观点,从而为李唐的诞生正名。
姚思廉父子是文人,对文人难免偏爱。《梁书》《陈书》中,光文人学者的传记就有七八十篇,且文从字顺,全用散文写成,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唐初骈文风头不减,连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也用骈文写成,姚思廉却用朴实洗练的散文语言把中唐的古文运动提前了近两百年。
这种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姚思廉却敢担当,因为他知道,任何时候都不缺能臣,缺的仅仅是创新且敢于坚持的人。以散文写史和慨然护主,在精神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脸谱人生
姚思廉的身份很奇特,除了修《梁书》《陈书》,除了道德感召,士子所推崇的政绩在他身上却寥寥无几。虽说他好史学,可他除了读书之外,没有其他嗜好,连生计也从不过问,但作为一个成功的男人,他下意识里肯定会对仕途发展有所期待。
作为十八学士之一,姚思廉想有所作为,因此他对政事曾采取直言无隐的方式进谏。这种刚直的姿态让太宗频频回眸。因为他虽然直言不讳,但方式灵活,让太宗接受得了――毕竟,他现在是帝王之尊,不是秦王了。这方式就是秘密上奏: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臣子尽了心,君王也不会难堪。
一年夏天,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正好被姚思廉看见。这种机会,姚思廉如何能错过,他当即上奏:“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把一场偶尔的释放上升到人品的高度,饶是太宗气量再大,也有失控的时候。他想发作,看看姚思廉的一脸凛然,又生生咽了回去,只得解释道:“朕有气疾啊,天气一热就病情加重,朕只是出来走一走,不是没事做整日游玩的。”作为善于纳谏的皇帝,他不仅要解释澄清,还得奖励人家正直敢言,太宗想了想,又赐帛50匹。
唐代的赏赐很丰富,有手工业品,如纺织品、金银珠玉、钱币等,有农畜产品,如谷物、茶叶和畜产品等,还有田宅。对姚思廉,太宗的赏赐很有意思:一律赐帛。从中可以看出太宗对姚思廉的态度:不轻不重,刚刚好。
姚思廉懂了:太宗对他很客气、很尊重,却不亲近重用。和那些大功臣相比,和其他的十八学士相比,他和太宗的关系终究有一层隔阂。于是,睿智如他,来了个人生急刹车。之后,史书对姚思廉的描写更是惜墨如金了,进谏肯定还有,只是或琐屑或敷衍,于他“没有政绩”的形象无补,连史书都不屑记载了。
世事难料,随着贞观盛世到了尾声,原先的功臣变成了鱼刺:玄武门之变的弑兄夺位让太宗一直有种道德挫败感,当初同谋的功臣在眼前晃悠更让他时时忆起那场梦魇。加之对他们功高震主的担忧,太宗终于祭起了宝剑:一方面亲自打压,一方面以孤臣魏征制衡。
这着棋的效果果然好:杜如晦郁郁而终,房玄龄如履薄冰……至此,十八学士已彻底成为明日黄花,唯独姚思廉依然清清爽爽。他本是外围人士,得意时不忘形,失意时也不为意,既然没有得到表演的舞台,他便躲到史书后,躲到太宗为他定制的脸谱后,冷眼看戏。
公元637年,姚思廉去世,享年80岁。太宗很悲痛,废朝一日哀悼,赐官、赐谥号,还准许他陪葬昭陵,誓将君臣情义进行到底。
相比于魏征死后被推倒墓碑,相比于虎头蛇尾的其他几位十八学士,姚思廉能善始善终,着实难能可贵。
这种幸运很大程度上来自李渊父子的捧场:一次偶然的机会,姚思廉粉墨登场,其个性化的演出正好契合李唐的审美需求。于是一个高大全式的先进典型诞生了:他成了一面旗帜,在舆论的猎猎大风中,引导着李唐战车从旷野驶向庙堂。
这种幸运更来自姚思廉对自我的清醒认知和定位:作为先进典型,他不能拒绝钦定的正面角色,虽说他也有潜力,能够出演更具挑战性和拓展性的其他角色;他更不能对这个角色有丝毫修正,因为任何旁逸斜出都是对皇权的无视和挑衅;他只能中规中矩地演下去,戴着忠勇的脸谱,戴着人生的假面……
在政坛风云变幻的时代,在茫茫宦海上,角色是舟,演技是帆,姚思廉终于安然渡到了人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