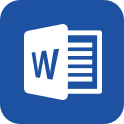摘 要:综观训诂学史,在清乾嘉前,占主导地位的是“因形求义”的形训,而至清干嘉时期,“因声求义”为作训诂的一个方法,比之“因形求义”更为重要,往往成为探求和贯通语义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清人;训诂;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之运用可上溯到先秦,然“因声求义”,系统化、理论化,应是在上古音韵系统完全明确以后方逐步形成的。清代是中国音韵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乾嘉学派尤精音韵,因而使“因声求义”发展为科学的训诂方法。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以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屈为病矣。”因此,“因声求义”往往成为探求和贯通语义的根本途径。
清初,顾炎武首先开辟了“因声求义”的坦途。戴震继起,更将音韵、训诂融会贯通,奠定了“因声求义”理论之基础。段玉裁继承戴震观点,进一步强调“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推动了“因声求义”这一理论的发展,王氏父子则更进一步强调“因声求义,不限形体”,使得这一理论走向系统化,科学化,而其他学者如朱骏声、程瑶田、阮元、郝懿行、钱绎、邵晋涵等人在此过程中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顾炎武提出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才是清人“因声求义”的真正开端。顾炎武把他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在文字形音义的考证中,声音是关键,顾氏正是抓住了声音这一关键,才做出了精当的考证。
戴震继承了顾炎武的音韵、训诂之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到声音与训诂关系,指出六类情况:“义由声出”、“声同义别”、“声义各别”、“异字异音绝不相通,而传写致讹,溷淆莫辩”、“本无其字,因讹而成字”、“字虽不讹,本无其音,讹而成音。”并看到谐声系统的重要性,指出谐声与假借的区别和联系,《答江慎修论小学书》中说:“六书之谐声、假借,并出于声。谐声依类附声,而更成字;假借依声托事,不更制字……后世求转注之说不得,并破坏谐声、假借,此震之所惑也。”
段玉裁将戴震“因声求义”主张运用于实践,使得这一学说更趋完善,他的《说文解字注》可谓是“因声求义”的典范。《说文解字注》研究范围之广,收集资料之多,可谓空前,还能从声义同源角度来探索谐声系统,这无疑是巨大进步。其次,段玉裁直接通过声训来阐明字义,包括直接以音同或音近字作注的声训。再者,段玉裁以声音贯串联绵词,他在《说文注》中,以古音为依据,正确的训释了许多联绵词,例如《说文・?部》:“旖,旗旖施也。”注曰:“许慎于旗曰旖施,于木曰旖,皆读如阿那……由此可知,以音为用,制字日多。广韵曰旖施,曰旖,……皆其俗体耳。”
王氏父子是“因声求义”集大成者。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全面阐述“因声求义”理论,并使其获得重大发展。清乾嘉以前,文字训诂研究重形不重音。王氏父子另辟蹊径,提出“声近义同”说,揭开了词汇研究的新篇章。王引之《经义述闻》说:“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今之学者,不求诸声,但求诸形,固宜其说之多谬也。”亦用此法系联同源词,具体方法是:音义结合法、右文法、声训法、音转法、综合法。同时亦考订通假字。《经义述闻・通说》中说:“许氏《说文》……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同时,他们考辩联绵词,《读书杂志》总结了连语的结构特点:“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旨。”王氏父子对联绵词的认识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同时运用于实践,这无疑是中国训诂史上重要贡献。
总观清人“因声求义”的理论,我们了解到“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在清代得到了系统的发展。但是在运用此方法时我们也需要注意运用古韵研究的成果,同时,在借助音韵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来说明声音变化的路线轨迹、解释声音变化的原因时,又不能拘守已定的韵部和声类。还需注意,运用“因声求义”方法应当十分谨慎,严格区分“音近义通”和“音同义异”两种不同的情况,万不可只凭主观臆断,妄下结论。离开古代文献的语言事实来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滥用假借,乱系同源,必然会违背词义在社会约定基础上的客观性,是非常危险的。
参考文献:
[1]陆宗达:《“因声求义”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6)。
[2]陈亚平:《清人“因声求义”述评》,应用语言学研究,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4)。
[3](清)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4。
[7](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407。
[8]陆宗达,《“因声求义”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