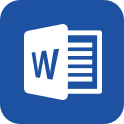近年来,国内“左派”一直批评自由派拿中国的缺点比别人的优点,自己则反其道而行之,竭力突出中国成就、夸大别国缺陷。今年早些时候,国内媒体同时抛出两篇文章,一篇警告“西式民主陷阱”,一篇“论证”“中国民主模式”。稍后,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发表《澄清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认知盲点》(刊于《北京日报》2014年7月7日)一文,宣称这些普世价值在西方长期是“少数人的特权”,只是近50年来才逐渐为不同种族和性别所共享。这些言论一面继续大唱“中国模式”赞歌,一面则想方设法渲染“民主危机”,竭力营造“风景这边独好”的氛围。其实,这些短篇评论自说自话、空泛无力、漏洞百出,只能算是舆论造势。迄今为止,在这个方面的最系统的代表作仍然是张维为自己的《中国震撼》。注1
这些反常识结论是如何产生的?我浏览了这部大作,大致梳理出以下七种方法,仅供那些不想被忽悠的读者参考。
二是在对象选择上以偏概全,专门“捡软柿子捏”。印度免不了是一个靶子,因为这个1950年立宪独立的国家几乎和当代中国同龄,却一直未能摆脱贫困。不仅印度,其他东南亚国家似乎也难逃西方民主的“厄运”。菲律宾是另一个经济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软柿子”:“美式民主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繁荣与富裕,而是动荡与贫瘠,国运也迅速由盛变衰。”注6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多数民众认为“民主转型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注7作者避而不提的是,英国、美国、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起飞恰和政治民主化同步,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并未阻碍其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更多取决于民主化的质量和社会稳定度。专制固然可以一时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是长远而言危机四伏;民主化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但是只要民主成果得以巩固,那么由此营造的长治久安必然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在因果归责上简单片面,把经济落后的过错统统归咎于民主制度。书中列数了印度民主的种种问题,譬如低效率――印度政府5年才改造了6000户贫民窟;譬如民主政体下的选民和政客受制于短期利益,不能从印度社会的全局长远利益出发,孟买的基础设施就因为局部利益牵制而长期滞后。再譬如民主政府心慈手软,为了赢得选举取悦选民,不敢控制人口增长,不能铁腕打破“既得利益”。注8种姓制度无疑制约了印度社会发展,而作者认为民主政治不如铁腕政治,无法消除罪恶的种姓制度,注9断言西方政治制度但求个性、不求共性,导致民粹主义盛行,印度社会分裂和严重失序,印度教派和穆斯林教派“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大规模冲突”。注10
民主政治确实容易受制于短期利益的掣肘,但是并不能对社会发展滞后承担全部责任。同样的体制,在不同文化的国家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实绩。种姓制度和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的国民性,人民习惯于安贫乐道的生活,而这是民主改变不了的。事实上,如秦晖教授指出,印度经济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长期推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注11而和民主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作者自己也承认,种姓制度与族群割裂并非民主政治本身的罪恶。从印度、美国等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宪政民主往往只能防止政府自身歧视,却无力杜绝社会自发的歧视。不妨换个角度,即便民主无力矫正传统之恶,威权专制的结果会更好吗?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彻底颠覆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本身即已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印度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60多年的和平统一已是极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大饥荒”“大革命”及各种折腾人民的政治运动;如果在印度实行威权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其实,民主的腐败再严重,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而之所以民主政治看上去腐败,专制政治却看上去“清廉”,往往是因为后者没有前者的新闻自由,挖掘腐败很难、风险很大。即便如此,公开发表的数据也不支持民主一定导致腐败的结论,尤其是在对照我们自己的情况之后。根据“透明国际”2013年统计的175个国家、地区的清廉程度排名中,中国排在第80位,处于中间位置,印度和菲律宾则并列第94名。说印度和菲律宾政治“腐败”,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照《中国震撼》的说法,东欧民主政治黑得暗无天日,但是数据显示并非如此:匈牙利排名
4
7、保加利亚排名77,所有东欧转型国家都比中国领先。注17作者说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腐败”,那么对中国的非民主政治该如何评价呢?更何况腐败调查难度很高,腐败“指数”主观随意性较大。如果被调查者知道中国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就能挪用上亿资金,一个能源部副司长就家藏数亿现金,中纪委现场核查竟烧坏好几部点钞机,注18恐怕中国腐败指数还会大幅滑坡。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并不为过。注19
五是单边抹黑、拒绝对照,在大肆抨击别人的时候闭口不谈自己的问题。譬如书中说到印度的“绿色指数”很差,却对中国自己的大规模生态环境破坏轻描淡写。我查了耶鲁大学公布的“环境表现指数”(EPI)。注20在2014年调查的178个国家、地区中,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瑞士、澳大利亚、卢森堡、新加坡、捷克。印度排名155,确实很落后,但是中国排名118,也好不到哪里。事实上,中国之所以综合指标优于印度,主要是因为环境的健康影响得到较好控制,气候与能源大幅度领先印度,而农业、森林、渔业资源均落后于印度,空气污染更是倒数第三(176名,印度174名),但是这些在书中均不置一词,或即便提到也都作为“前进中可以克服的困难”一带而过。
六是曲解别国制度,混淆视听。《中国震撼》诋毁新闻自由,为的是说明哪个国家的新闻自由都不是绝对的:“美国不允许报道本・拉登讲话,英国不允许歌颂希特勒,日本不允许批评天皇,泰国不允许开国王的玩笑。”注21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禁止报道本・拉登讲话的法律;之所以看不到拉登讲话,是因为主流媒体不会长篇累牍地报道一个恐怖分子头目的原话。英国禁止的则是否认犹太大屠杀存在的事实,而不是歌颂希特勒的评论;歌颂还是谴责任何人,是公民自由选择的价值取向,是国家不能禁止或强求的。日本和泰国确实不允许批评天皇或国王,但那只是一条单独的禁令而已,能否和全面管控媒体、直接给媒体下指令控制内容相提并论呢?以此来论证“哪个国家的新闻都不自由”,只能是混淆视听。而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在新闻自由和网络言论上的排名比民主指数更靠后。
《中国震撼》一书问题实在太多。我不是要一概否定《中国震撼》或任何一种国内左派观点。《中国震撼》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其观点的说服力,而在它可以让我们反思民主体制本身的问题,尤其是为什么印度民主发展得相当不错,却不仅长期陷于贫困,而且也未能保护环境?事实上,西方学者也在不断反思和批评自己的体制。这种现象本身表明宪政体制的健康。无论设计多么完美的制度,在实践过程中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有缺点、弱点,因而需要批评监督,如此才能纠正错误、不断进步。不幸的是,国内不少“左派”投机取巧,把民主体制所容忍的自由批评当作抹黑民主的污点,抓住一点、无限夸大、混淆视听。其实要写问题,中国的公权腐败、强征血拆、环境破坏……能写出多少本书来?一旦国内的批评声音遭到压制,民众对国外的情况又不明就里,诸如《中国震撼》及国内某些媒体所带来的舆论误导就尤其值得警惕了。
不论国内“左派”对民主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民主都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儿。与其诋毁民主、弘扬“国粹”,刻意找一些民主不成功的国家作为逃避民主的心理安慰,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来“论证”某个既定的结论,不如正视自己的问题并对症下药。毕竟,别人好不好终究是别人的事;自己得了病却拒绝吃药,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